标签:
中华书局, 行业资讯, 古籍杂谈
中华书局, 行业资讯, 古籍杂谈
来源:出版人杂志微信公众号 作者:张北
业精于勤,而贵以专。治学如此,做出版同样如此。
20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00周年之际,徐俊出版了《敦煌诗集残卷辑考》,首次完成全部敦煌遗书中存世诗歌的整理,这部作品代表了当时敦煌诗歌研究的前沿水平,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代表著作。时隔十余载,已是中华书局总经理的徐俊再推力作《鸣沙习学集:敦煌吐鲁番文学文献丛考》,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评价此书,“引证之丰沛,考辨之绵密,分析之仔细,发明之新警”。而在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的眼中,徐俊是一位专业的学者,更是一个优秀的职业出版人,“一个专业的学者未必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职业出版人,但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则不能不专业”。
继入选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和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之后,徐俊新近荣膺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
在编辑学者化的环境中成长
1983年,徐俊如愿以偿,被分配到中华书局工作,并与文论专家、资深编辑周振甫成为同事。“1980年代的中华,充溢着一种求知向学的风气。”徐俊记得,周先生每次有新著出版,必签名送给编辑室每一位同事。“周先生是学者型编辑的代表,那时候,中华的老辈编辑如杨伯峻、王文锦、赵守俨,都有专精绝学。中年一代如程毅中、傅璇琮先生,他们的著述,在学术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当时徐俊所在的文学编辑室每个人都有专业分工,得益于前辈的指引和同事的砥砺,为他人做嫁衣的同时,也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不断积累。
1986年前后,因为承担责编陈尚君《全唐诗补编》的机缘,徐俊开始接触敦煌文学文献,并尝试对敦煌诗歌写本进行系统普查。当时中华书局还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36号办公,这里离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不远,而书局自己的图书馆馆藏也十分丰富。徐俊接到书稿的第一件事就是“泡”图书馆,查阅当时学术界已经发表的《全唐诗》订补之作,确定编辑工作重点。其间系统翻阅了140册的《敦煌宝藏》影印本。到1991年,徐俊基本完成敦煌诗歌写本的查考和校录。经过一再修改补充,2000年6月《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正式出版。

专业化是中华书局这家百年老店的传统
无论是治学还是编书,“小扣则大鸣”的周振甫等老一辈编辑的言传身教,给徐俊的影响至深。虽然曾有机会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但徐俊2003年奉调回到书局,选择在编辑出版这个平台上尽责履职,“对于我们这些多年从事出版的人来说,虽然学问心还在,但做出版是更合适的选择,能够更大地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
徐俊告诉记者,过去书局提倡编辑学者化,现在我们提倡编辑专业化,专业化是中华书局的传统。“编辑要对自己所在的出版板块、所负责的学科,长期跟踪,深度介入,有对学术的基本判断能力,才能真正服务学术、服务作者。”在中华书局,编辑人员参与古籍整理出版,独立完成古籍整理项目,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工作,并非个案,而是书局延续至今的传统。“古籍整理是经验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做过和没做过完全不一样。我们这辈人处在过渡期,在历年的工作实践和积累中,延续了老一辈的传统。而年轻一辈尤其是近几年入职书局的硕士和博士生,他们的专业背景和提升机会,都比我们这代甚至前一代人更好。书局近年来一些重点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的出版,得益于年轻一代的努力,也助推了年轻一代的成长。”
“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
中华书局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权威版本。然而受当时客观条件所限,加之整理出版历时绵长,参与点校者变动,点校标准和体例未能统一,整理深度各有参差,各史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憾。为适应新时代学术发展和读者使用的需求,这部大书亟需全面修订。
2007年,“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修订工程正式启动。由于各史点校本情况复杂,作为工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徐俊,必须做到心中有数,从修订总则起草和承担单位遴选,到各史修订方案制定,包括底本选择、修订体例、样稿审读,以及出版后的宣传营销,徐俊全程参与了工程的组织和出版工作。“以程序保证质量。”编辑组对每一条校勘记、每一处改动都要认真复核。对于有争议的问题,编辑组与修订组要集中讨论,徐俊几乎从头到尾参加每一次讨论会,共同商定问题处置办法,重要环节绝不假手于人。每一史的修订稿,书局都要请十几位专家外审,徐俊对每一位专家的意见都会认真阅读核查,按照修订体例予以鉴别吸收。

每一部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的问世都经历了重重审核
几乎每一史修订本问世,徐俊都会做深度访谈,在发掘和肯定老一代整理者贡献的同时,也对新一代修订者的贡献予以充分表彰。近几年来,中华书局局史是他关注最多的一个方面,围绕局史上重要的书和人,写下了十几万字的文章。在他看来,研究敦煌诗歌和书局局史都因工作而起,因工作需要,摸索学习,形成了自己的一点学术成果。“作为书局的编辑,不一定也不可能都去当学者,但个人的学问心不能丢,对学术标准的追求不能丢。”
目前,“二十四史”修订本的《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书》、《南齐书》已经先后出版,修订本《宋书》、《隋书》、《金史》等即将面世。值得欣慰的是,古籍整理逐渐受到全社会更多的关注和肯定,继摘得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一等奖后,《史记》修订本又获得了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和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图书奖。除了“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工程,这几年徐俊主抓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敦煌经部文献合集》、《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等重点图书,也先后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不专业无产业
潘凯雄在为《鸣沙习学集》写的书评中提出,不专业无产业。他认为,优秀出版人之专业至少应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对自己所在出版领域的学术专业,二是对出版本身的职业专业。
徐俊表示,学术专业和职业专业二者兼长是个人和团队都不应该放弃的追求,但在不同的产业环境和发展时段中,其标准是不一样的。“出版是内容产业,好的出版人应该是出版领域的行家里手,对内容要有判断力和把控力。”中华书局始终坚持守正出新,“计划经济时代,古籍整理出版的标准主要是学术标准,以国家古籍整理规划为指针,逐年积累。现在产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专业出版所面临的学术研究和读者需求都发生了变化,如何在新的上下游环境下优化和调适我们自身的工作,实现两个专业结合,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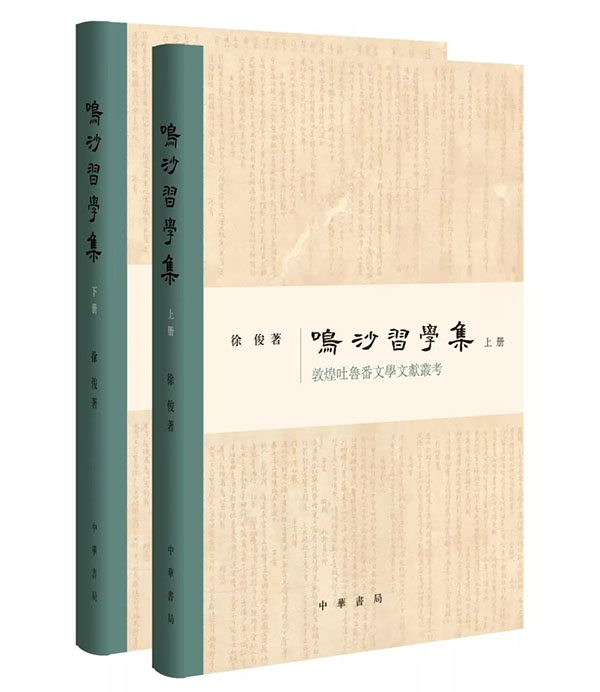
徐俊所著《鸣沙习学集》为敦煌吐鲁番文学的重要专著
徐俊说,中华书局作为传统文化出版重镇,其最大的特征和优势就是专业性,集中体现在重大项目带动和“基本书”理念两个方面。“发挥重大项目的带队作用,在古籍整理学术出版行业保持领先地位。所谓领先,不是简单地比重点项目和获奖数量,而是要围绕国家战略,服务学术,引领读者,聚集资源,保证核心品牌发展,并带动骨干人才成长和专业队伍培养,推动古籍整理学科和传统文化产业的建设和成长。”
中华书局近年来在传统文化大众出版方面的成功探索有目共睹,徐俊告诉记者,“除了重大项目,我们还坚持出版基本书和‘小书’”。一些“小书”可能永远无缘获奖,甚至申请不到古籍出版补贴,也很难快速得到市场回报,但从长远来看有益于书局出版体系的建设,是学科建设所需,即使销量少也要做。“传统文化大众出版同样强调基本书理念和体系建设。所谓的大众书实际都是小众书,大众书是个泛概念,其实是精准的小众。”中华书局一直强调要以专业的精神和标准来做大众出版,这也是其传统文化大众图书能够占领市场的根本原因。“体系建设、内容原创、形式创新、质量保障,这四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大众出版才能走得更远。”这几年,书局重印书的品种数和销售量占比都很大,得益于产品的有效积累,是专业化保证了细分市场的位置。此外,中华经典古籍库等数字出版产品,同样体现出书局的专业水准。
基于多年来的实践和积淀,专业化的传统早已融入了中华书局人的血脉中,书局的品牌影响力得以不断提升。对于书局未来的发展,徐俊指出,有几个大方向一定要坚持。一是坚持传统文化的出版方向和“同心多元”的产品战略。二是坚持古籍整理基本书理念,继续做好原创和深度整理同时,鼓励适应新形势的后出转精和更新迭代工作。三是坚持大力推动传统文化大众出版,既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满足时代需求。“尽出版的社会责任,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企业自身。”